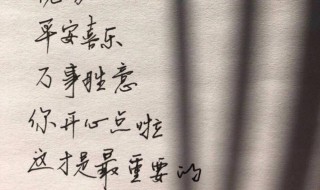今年,近60,000名无证,无人陪伴的儿童越过南部边界进入美国,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并引发了激烈的政治辩论。这些孩子应该被赋予精神和法律权利吗?我们应该为他们的苦难感到同情吗?

面对如此巨大的危机,人们常常想到特蕾莎修女的路线:“如果我看着群众,我将永远不会行动。” 大量受害者似乎不知所措,难以思考,通常被视为冷门统计。这种反应似乎揭示了移情的能力限制:同情比单个受害者(例如被困在井中的小杰西卡)更容易受大型受害者(例如成千上万的边境儿童)的影响。我们似乎对数字麻木。这种缺额之所以惊人,是因为许多人认为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会感到更多的同情,并且他们有义务这样做。当最需要同理心时,它就会失败。
最近,包括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哲学家杰西·普林茨(Jesse Prinz)和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内的许多作者都认为,由于移情偏向可识别的受害人,因此在做出道德,法律和政策决策时不应信任移情。正如布鲁姆所说,“同理心狭窄;它使我们与特定的人联系在一起,无论他们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但对数值差异和统计数据都不敏感。” 正如普林兹(Prinz)所说,“我们为有需要的邻居做出的贡献要比因遥远的海啸而遭受破坏的数千人或因饥饿或疾病而丧生的数百万人……在制定政策时,我们最好不理会同情。”
但是,如果移情的界限不是一成不变的怎么办?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对移情的看似固定的限制可能是可塑的。换位思考的失败可能反映了为避免换位思考而做出的积极选择。正如批评家所言,同情本身可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人们为避免移情而做出的选择。
首先,定义同理心很重要。当心理学家讨论共情的极限时,通常指的是“情感共情”:他人经验的替代性分享(即“感受”,如果你不高兴,我会不高兴)。移情会导致很多反应,包括同情心:激发亲社会行为的另一种集中情绪(即“感觉”,如果您不高兴,那么我想减轻您的痛苦)。批评家通常关注同情的极限,但暗示同情是一件好事。然而,对同一个受害者的偏见因同情和同情而出现。我称这种效应为“同情崩溃”,但对于同理心和同情心都可能发生。
考虑到这些定义,很多工作表明同情的限制可能是出于动机,而不是固定的。我最喜欢的解释这一想法的轶事借鉴了莎拉·麦克拉克伦(Sarah McLachlan)主演的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著名广告。两分钟的视频(您可以在此处选择观看)将麦克拉克兰(McLachlan)对“天使的怀抱”的演绎形式呈现给受虐待的幼犬和小猫。尽管我坚决支持动物权利,但我发现很难收看广告,有时会关闭它,以免遭受痛苦而在精神上筋疲力尽。正是因为我关心他们的福利,所以情感代价如此之高。甚至Sarah McLachlan也说过 她在进行广告宣传时会改变渠道,以避免被自己的情绪所淹没。
这是激励情绪调节的一个例子:改变情况以避免代价高昂的同理心。但是轶事不是数据,许多心理学实验都支持这种观点。二十年前,一组研究表明,如果人们认为帮助会导致高昂的同情心,那么他们会避免听到对引起强烈共情的帮助的呼吁。最近,我检查了动机调节是否可以解释同情崩溃。如果人们预测随着数字的增加会有更多的情绪,这可能会引起对财务和情绪成本的担忧,从而导致同情回避。在一项实验中,我们让参与者阅读了达尔富尔的一到八名儿童难民。一半的参与者希望捐款,另一半则没有。当参与者希望捐款时,他们倾向于对一位受害者比八位受害者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但是当这笔费用被取消后,他们对八名受害者的同情心多于一位受害者。改变动机以避免同理心使同情心崩溃。我们还发现同情崩溃只会出现在熟练的情绪调节者身上,这表明情绪调节对于这种情绪的出现是必要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对大量数字不敏感,但这可能不是容量限制:相反,
Bloom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经历别人的痛苦会导致精疲力竭和倦怠。” 这种情感上的代价可能会激发共情调节,实际上,医生似乎在调节共情来避免这种代价。我的实验室目前正在探索用尽成本如何导致我们使他人不人道。正如爱荷华州作家工作室校友莱斯利·贾米森(Leslie Jamison)在对布鲁姆的回应中所说的那样 ,“如果倦怠和疲惫是过度同情的危险,那么抽象就意味着过少的危险。”
对同理心的积极进取的观点在该领域越来越受欢迎。 自恋者和精神病患者 往往对他人表现出较少的同情心,但是指示他们同情心可以减少这些缺陷。人们对同理心的看法也很重要:那些相信可以培养同情心而不是固定同理心的人会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感受到同情心。这项工作与关于自我控制的发现相类似:有些人声称自我控制是能力有限的资源,而另一些人则表明,自我控制的局限性只出现在那些相信自我控制是有限的人身上,这表明动机具有一定作用。。
简而言之,我们不要为避免这种情况而做出的积极选择归咎于同情。在某些情况下,同理心只会受到我们所希望的限制。